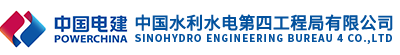山一程 水一程 |
|
|
|
|
接到任務那天,尚義已經將要入冬。 彼時我正在為電站即將迎來下水庫下閘蓄水和地下廠房四臺機組混凝土機層全面封頂兩大節點奮筆疾書,也在為即將開始的采風之旅焦慮。QQ的企鵝不停閃動,對話框里“青年論壇”“創新工法”的消息傳來,像一枚石子投進深潭——每個詞都閃著光,每個光點都映照著我這個文科生的惶然。無排架?一機多用?高陡邊坡?我把這些詞在唇齒間反復咀嚼,像辨認異國的文字。筆記本上,剛寫下的“高臂鉆機”旁邊,還留著昨日讀書筆記里“普魯斯特的追憶”的墨跡,兩個世界的詞匯在此相遇,中間隔著我無所適從的白天黑夜。 于是開始鑿壁借光。“志慧姐,這個一機多用的主要改裝就是頂部鎖定機構嗎?”“施工效率提升的計算是以什么為標準?設備可靠性是否經過反復實驗論證?”“無排架技術相對成熟的背景下,我們的創新點是什么?”……已經記不起多少個夜晚,多少次提問,但又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讓我這顆忐忑的心多點底氣和安全感。把論文讀成散文,把圖紙看作山水。深夜的臺燈下,我給每臺冰冷的機器起溫暖的名字:那伸著長臂的YD225鉆機是“巡山者”,那可變換孔徑的QCMG-18是“千面手”。我在工法的邏輯里尋找詩的結構——四區協同是起承轉合,分級加載是層層遞進。原來工程技術里住著嚴謹的浪漫,那些力與美的平衡,何嘗不是另一種修辭? 11號出差,10號早上嗓子忽然開始發炎,我一邊給濤哥發消息說好怕比賽當天醒來一張嘴“寶娟,我的嗓子”,一邊開始含化甘草片,以前用水吞服都吞不下的藥,現在一天含化了12片,似甜又苦的味道在舌尖化開,沖得人不敢說話。可即使是這樣,發燒還是來了。10號晚上開始發燒,不高,但低燒不退,11號的高鐵一路向北,窗外的平原漸漸有了山的骨骼。我在座位上裹緊外套,額頭滾燙,卻還在默念著那些剛剛熟悉起來的術語。入住的酒店房間里,退燒藥和講稿攤在一起,水杯旁散著潤喉糖。發燒帶來的眩暈里,PPT上的文字時而模糊時而清晰,像隔水觀花。但奇怪的是,當身體最不適時,心里反而生出一種奇異的清明——既然已山一程水一程地來了,便沒有退路。 抽到二號出場時,掌心還有低燒的余溫。站在臺上,燈光如瀑的剎那,我腦子里忽然有點空白,只是看著臺下一雙雙專注的眼睛,肌肉記憶一般的講稿開始涌現。我開始講述,講述如何讓機械長出臂般協奏。講到“我們拔除了這把限速器,換上了一套真正四位膀,如何讓施工像作曲一體的加速引擎時”我看見了評委眼里的光,那一刻,文科生的軟肋長成了鎧甲——我們本就更懂得如何讓堅硬的技術擁有溫柔的表達。 接過二等獎的證書獎杯時,尚義的冬已經來了。但我帶著無數四局尚義人上千個日夜實踐出的成果,站在了公司的領獎臺,我在,他們便在。 這一程,像一次笨拙的朝圣,帶著書本里的詩意,闖入鋼筋水泥的森林,卻發現這里也有星空。那些啃讀圖紙的長夜,那些帶病堅持的路途,都化作證書上隱形的花紋。山一程,是攀登知識壁壘的艱辛;水一程,是跨越學科鴻溝的流淌。而最大的獎賞,是在陌生的疆域里,遇見了另一個可能的自己。原來所有的成長,都是先在荒原上種花,再等花開成海。 |
|
|
|
| 【打印】 【關閉】 |